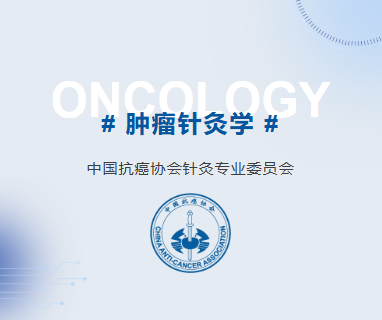[1]周小翠,王立玉,季锋等.揿针联合阿片类镇痛药物治疗中重度癌性疼痛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β-内啡肽、P物质水平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杂志,2023,57(01):71-75.
[2]Faria, M., Teixeira, M., Pinto, M. J., & Sargento, P. (2024).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on cancer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2(3).
[3]卢静,刘晓蒙,陈莹等.从心身同治角度针灸对乳腺癌关节痛患者生命质量改善的临床研究[J].世界中医药,2023,18(02):249-254.
[4]袁永,黄涛,邱国同等.围手术期电针减少胃及胰腺癌患者术后止痛药物使用的随机对照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03):1396-1400.
[5]Shen G, Ren D, Zhao F, et al. Effect of Adding Electroacupuncture to Standard Triple Antiemetic Therapy on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4;42(34):4051-4059.
[6]李文涛,刘阿庆,张冠,等. 三焦针灸法对中晚期胃腺癌癌因性疲乏的疗效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J]. 实用肿瘤杂志,2023,38(03):270~275.
[7]王芹,王立玉,周迪,等. 针刺配合中药治疗气血亏虚型肺癌癌因性疲乏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23:1~6.
[8]黎翠玲,李翔,卢园园,等. 电针联合刺络放血治疗乳腺癌化疗性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研究[J]. 现代中医药,2023,43(04):65~69.
[9]Huang M, Chang S, Liao W, et al. Acupuncture May Help to Prevent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A Randomized, Sham-Controlled, Single-Blind Study.[J]. The oncologist,2023,28(6):e436~e447.
[10]Chan K, Lui L, Lam Y,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lectroacupuncture for oxaliplatin-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 single-blinded, randomized, sham-controlled trial.[J]. Acupuncture in medicine : journal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cupuncture Society,2023,41(5):268~283.
[11]赵薇,张宏如,陆萍,等. 力动针结合功能锻炼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随机对照试验[J]. 中国针灸,2023,43(10):1123~1127.
[12]Wang C, Liu H, Shen J, et al. Effects of Tuina Combined With Moxibustion on Breast Cancer-Related Lymphedema: A Randomized Cross-Over Controlled Trial.[J]. Integrative cancer therapies,2023,22:1563487871.
[13]Lu C, Li G, Deng D, et al.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Warm Acupuncture for Breast Cancer Related Upper Limb Lymphedem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2023,29(6):534~539.
[14]Wang Y, Yang J, Yan S,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vs Sham Electro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Ileus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surgery,2023,158(1):20~27.
[15]Ru O, Jin X, Qu L, et al. Low-intensity transcutaneous auricular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reduces postoperative ileus after laparoscopic radical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Minerva anestesiologica,2023,89(3):149~156.
[16]何佩珊,姜敏,杨公博,等. 针刺防治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术后胃肠功能紊乱的临床疗效[J]. 世界中医药,2023,18(05):658~661.
[17]Zhong B, Shi C, Xu D. Effect of acupoint stimulation on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for intraoperative frozen section analysis.[J]. Technology and health care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2023,31(5):1683~1689.
[18]梅荷婷,卢雯平,常磊,等. 疏肝调神法治疗原发性乳腺癌合并广泛性焦虑障碍的随机对照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1~19.
[19]王宏君,孙亚男,王晓燕,等.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结合针刺治疗恶性肿瘤相关性失眠的效果观察[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3:1~12.
[20]方文娟,李红,周丽丽,等. 针刺联合耳穴贴压治疗骨髓瘤伴失眠的疗效观察及对认知功能、睡眠质量的影响[J]. 上海针灸杂志,2023,42(11):1157~1161.
[21]Zhang J, Qin Z, So T H, et al. Acupuncture for chemotherapy-associated insomnia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 assessor-participant blinded, randomized, sham-controlled trial.[J]. Breast cancer research : BCR,2023,25(1):49.
[22]吴子婷,刘妮,张亚男,等.基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探讨针刺治疗乳腺癌化疗相关认知障碍的脑机制[J].中医杂志,2024,65(05):495-502.
[23]Wang W, Liu Y, Yang X, et al.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for Opioid-Induced Constipat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China: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network open,2023,6(2):e230310.
[24]李丹, 胡凯文, 韩丽, 赵百孝. 艾灸对癌性疲劳小鼠免疫神经内分泌的影响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04): 1799-803.
[25]李丹, 胡凯文, 韩丽, 赵百孝. 艾灸对癌性疲劳小鼠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的影响 [J]. 世界中医药, 2024, 19(19): 2924-30.
[26]吕转, 刘瑞东, 苏凯奇, et al. 针刺对乳腺癌癌因性疲乏模型小鼠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3, 25(07): 2402-11.
[27]刘瑞东, 王泽鹏, 冯晓东, et al. 针刺对乳腺癌化疗后癌因性疲乏模型小鼠肠-脑轴相关因子的影响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24, 34(08): 21-7.
[28]王文哲, 魏星宇, 于冬冬, et al. 针灸调控TNF-α/TLR4/NF-κB改善顺铂小鼠肝损伤的作用机制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3, 25(03): 1055-60.
[29]马强, 于珊珊, 孟杰, et al. 电针联合泮托拉唑对乳腺癌裸鼠免疫功能、病理形态及CYP17/CYP19表达的影响 [J]. 针灸临床杂志, 2023, 39(10): 68-75.
[30]常馨, 卢涛, 黄金昶. 电针围刺诱导小鼠乳腺癌微血管正常化的初步研究 [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3, 54(05): 972-7.
[31]董芹作, 邢利威, 余顺, et al. 基于EGFR/STAT3途径探讨经络辨证逆针灸干预乳腺癌发生过程的作用机制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10): 5514-8.
[32]徐森磊, 陈静, 陶李蕙苹, et al. 瘤周围刺电针调控三阴性乳腺癌铜死亡增敏化疗疗效的作用研究 [J]. 针刺研究, 2024, 49(11): 1153-9.
[33]张飞程, 高田宇, 张晨曦, et al. 灸药联合对乳腺癌荷瘤小鼠肿瘤组织免疫检查点的影响研究 [J]. 针刺研究: 1-15.
[34]乔宇, 薛晓红, 杨茗橘, et al. 艾灸通过TGFβ1/TSC22D1信号通路干预乳腺癌化疗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机制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09): 4612-8.
[35]阎旻宇, 李冰融, 蒋君涛, et al. 薏苡附子败酱散联合电针治疗对AOM/DSS小鼠炎症相关性结直肠癌的防治作用及机制 [J]. 现代肿瘤医学, 2023, 31(13): 2405-11.
[36]方杰, 吴叶琪, 黄雪燕, 王睿. 基于microRNA探讨电针延缓HepG2裸鼠荷瘤生长趋势效应的初步机制 [J]. 中国中医药科技, 2023, 30(01): 8-13.
[37]姚重界, 祁琴, 赵继梦, et al. 针灸调控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大鼠结肠肿瘤增殖相关的circRNA表达谱的研究 [J]. 上海针灸杂志, 2024, 43(11): 1257-68.
[38]董芹作, 李襄, 杨隽, et al. 经络辨证逆针灸对二甲基苯蒽诱导的大鼠乳腺肿瘤发生过程的影响 [J]. 辽宁中医杂志, 2023, 50(02): 181-5+225-6.
[39]刘石美, 韩芳, 牛天慧, et al. 艾灸对豚鼠血清TNF-α、IL-6、CCL22表达的影响 [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24, 23(15): 1573-6.
[40]马强, 于珊珊, 孟杰, et al. 穴位刺激联合COX-2抑制剂对乳腺癌骨转移大鼠镇痛、NK细胞活性及PK2蛋白水平的影响 [J]. 针灸临床杂志, 2023, 39(09): 80-6.
[41]关伟强, 于冬冬, 王文哲, 王建明. 针灸对CTX骨髓抑制模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骨髓细胞中hMLH1和hMSH2基因的影响 [J]. 中医研究, 2023, 36(04): 75-7.
[42]宋亚芳, 张晓梅, 蒋诗媛, et al. 从肠道菌群探讨艾灸“足三里“”肝俞”穴抑制裸鼠结肠癌细胞肝转移机制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24, 26(12): 3118-26.
[43]严景妍, 刘志勇, 龚安, et al. 腹针调控水、盐、糖代谢治疗慢性心理应激肺癌荷瘤小鼠实验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09): 4965-71.
[44]张慧, 张娟. 针刺联合穴位贴敷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疗效观察及对楔状组织中TGF-β1/Smad信号通路的影响 [J]. 新中医, 2024, 56(12): 163-70.
[45]李泽丽, 曾文静, 李国海, et al. 电针“足三里”联合capeOX方案对结直肠癌裸鼠肿瘤细胞凋亡和铁死亡的影响 [J]. 针刺研究, 2024, 49(07): 678-85.
[46]阳国彬, 刘玉芳, 李佳, et al. 中药联合针刺对脾虚型胃癌前期病变模型大鼠的实验研究 [J]. 中医药信息, 2024, 41(04): 40-4+54.
[47]LI J, FU R, GUO X, et al. Acupuncture improves immunity and fatigue after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y inhibiting the Leptin/AMPK signaling pathway [J]. Support Care Cancer, 2023, 31(9): 506.
[48]张学君, 林久茂, 陈诗兰, et al. 电针“足三里”减轻大肠癌荷瘤小鼠5-FU化疗后肾损伤及其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的研究(英文) [J]. World Journa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2023, 33(03): 244-51.
[49]MAO N, WU X, WANG C, et al. Effect of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Cisplatin o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Hypoxia and Vascular Normalization in Lewis Lung Cancer Mice [J]. Integr Cancer Ther, 2023, 22: 15347354231198195
[50]TIAN S X, XU T, SHI R Y, et al. Analgesic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bone cancer pain in rat model: the role of peripheral P2X3 receptor [J]. Purinergic Signal, 2023, 19(1): 13-27.
[51]NGUYEN T V, CHIU K C, SHIH Y H, et al. Protectiv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Chemotherapy-Induced Salivary Gland Hypofunction in a Mouse Model [J]. Int J Mol Sci, 2023, 24(14).
[52]ZHANG X J, LIN J M, LIN C J, et al. Protectiv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at ST36 against damage of intestinal mucosa,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5-FU chemotherapy in mice with colon cancer [J]. Zhen Ci Yan Jiu, 2023, 48(12): 1249-57.
[53]LI J, HAN Y, ZHOU M, et al. Electroacupuncture ameliorates AOM/DSS-induced mice colorectal cancer by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and promoting autophagy via the SIRT1/miR-215/Atg14 axis [J]. Aging (Albany NY), 2023, 15(22): 13194-212.
[54]Epstein AS, Liou KT, Romero SAD, et al. Acupuncture vs Massage for Pain in Patients Living With Advanced Cancer: The IMPAC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Netw Open. 2023;6(11):e2342482. Published 2023 Nov 1.
[55]Jeong YJ, Choi HR, Kim KS, Shin IH, Park SH. Impact of Acupuncture on Hot Flashe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Adjuvant Antiestrogen Therapy with Tamoxif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Integr Complement Med. 2023;29(4):241-252.
[56]Ben-Arye E, Hausner D, Samuels N, et al. Impact of acupuncture and integrative therapies on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A multicenter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Cancer,2022,128(20):3641~3652.
[57]D'Alessandro E G, Nebuloni Nagy D R, de Brito C M M, et al. Acupuncture for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ilot study.[J]. BMJ supportive & palliative care,2022,12(1):64~72.
[58]Tong Q, Liu R, Gao Y, et al.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Based on ERAS for Preoperative Anxiety in Breast Cancer Surgery: A Single-Cen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Clinical breast cancer,2022,22(7):724~736.
[59]Azevedo C, Ferreira da Mata LR, Cristina de Resende Izidoro L, de Castro Moura C, Bacelar Assis Araújo B, Pereira MG, Machado Chianca TC. Effectiveness of auricular acupuncture and 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following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rostate canc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Eur J Oncol Nurs. 2024 Feb;68:102490.
[60]Michel-Cherqui M, Ma S, Bacrie J, Huguet S, Lemaire N, Le Guen M, Fischler M. Auriculotherapy and acupuncture treatments for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a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Support Care Cancer. 2024 Jul 31;32(8):560.
[61]Paiva EMDC, Moura CC, Nogueira DA, Garcia ACM.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uricular Acupuncture Protocol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in Cancer Patients. Healthcare (Basel). 2024 Jan 16;12(2):218.
[62]Sørensen RW, Andersen NI, Dieperink KB. NADA Acupuncture in Specialized Palliative Care: Patients' and Family Caregivers' Experiences. J Pain Symptom Manage. 2024 Jul;68(1):1-9.
[63]Yildirim D, Kocatepe V, Talu G K. The efficacy of acupressure in managing opioid-induced constipation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A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2022,30(6):5201~5210.